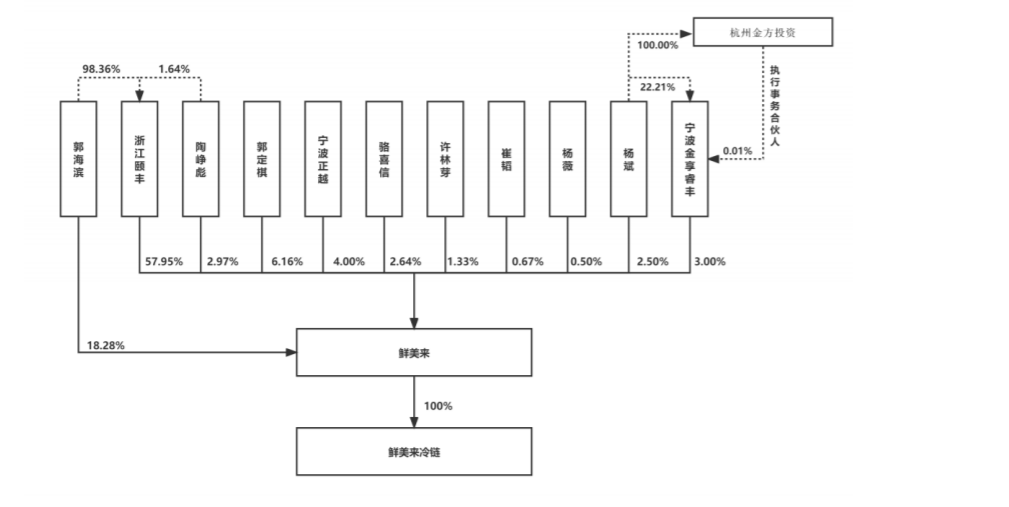学术前沿于晓利茨维塔耶娃诗学世界的统一性——从作品主题、语言形式、文化传统层面的分析糌粑袋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点击俄罗斯文艺关注我们
茨维塔耶娃诗学世界的统一性*
——从作品主题、语言形式、文化传统层面的分析
于晓利
*本文系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茨维塔耶娃长诗中的存在命题》(编号:2014-GH-632)阶段性成果。
摘要小米袋日常生活与存在(бытие)的矛盾贯穿于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的始终,并呈现在多个层面上。在主题上,诗歌中爱情、死亡、艺术等核心主题具象地展现了诗人意识里生活与存在的矛盾,并勾连起诗人前前后后的作品;在语言形式层面,相似性联想的形象、相同的词语或意象、词语的谐音等语言形式的反复出现加强了诗歌语意表达的力度,同时串联起诗人创作中的多重主题;在对传统的继承方面,茨维塔耶娃的诗在寻求个人声音的自由和个性之时,不自觉地受到她所接触的本民族乃至整个西方文学文化传统的向心影响,实现了个人诗作与文化传统的传承。这些无所不在的交织关联共同构成了诗人完整统一的诗学世界。
关键词茨维塔耶娃 日常生活 存在 统一
茨维塔耶娃被认为是俄国白银时代最特立独行的女诗人,她不参与任何文学流派和团体,不关注周遭的社会变革,不遵循固有的诗歌创作模式和准则。她的创作是自然的创作[1](5)小米袋,聚焦于内心世界,描写每一个真实的瞬间,描写她在时间与空间风云变幻之中内心状态的起伏。现实的诸多痛苦和对理想的精神世界的向往,日常生活与存在(бытие)的矛盾贯穿于诗人创作的始终,成为关联着她的一生、关联着诗人与语言、个人与传统、现实与记忆的链条,这种无所不在的连接有如一张结实的网,支撑起了诗人的整个诗歌世界。
日常生活与存在的矛盾活跃在茨维塔耶娃诗歌的各个层面。首先,在诗的主题上,无论是她少女时代对青春、爱情和自然的歌咏,还是中年时期对生命、死亡、艺术的叹息,诗人诗歌中多重主题的变奏无不与日常生活与存在的矛盾密切关联。爱情、死亡、艺术等核心主题在多首诗中的反复呈现将诗人的作品串联起来,日常生活与存在的矛盾沿着诗人的诗歌创作轨迹延伸,直至生命的终结。其次,在诗的形式上,茨维塔耶娃的诗在标题或第一行给出核心形象,之后开始一连串相似性联想的形象,构成了隐喻的链条;[2](239)小米袋相同的词语或意象出现在前前后后的诗中,形成诗歌语言形式上的反复效果;此外,诗人晚期诗歌中采用的词语或多或少存在声音上的接近和涵义上的联系,这些联系构成了一张结实的网,共同验证着诗的主题。最后,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既有对俄国文学经典和德国浪漫主义的继承,又浸染着浓郁的宗教文化色彩,还有对古希腊罗马神话精髓的吸取,实现了个人诗作与文化传统的传承。这些无所不在的交织关联证明了茨维塔耶娃的创作主题、语言形式以及个人创作与世界文学传统之间都是统一的、一致的,这些关联共同构成了诗人完整统一的诗学世界。
▲Марина Ивановна Цветаева
✦✦
一、
主题层面的统一:日常生活与存在
从19、20世纪的俄国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中,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诗人作家们试图摆脱尘世烦扰超越当下现实,渴求彼岸永恒的心灵世界、试图追寻存在的真谛。日常生活与存在是俄国文学永恒的命题。[3](103)小米袋茨维塔耶娃饱读俄国优秀诗人的作品,接触德国浪漫主义的经典,她的灵魂深处有着终生不衰的浪漫主义精神。茨维塔耶娃的大部分诗聚焦于对青春、爱情、自然、生命、艺术、死亡、上帝的感悟,是诗人内心日常生活与存在矛盾不断发展的结果和多方面呈现,可归结为:现实生活和诗歌世界的冲突、尘世之爱和灵魂之爱的矛盾、生与死的抉择等。
茨维塔耶娃的整个诗歌轨迹都是对日常生活与存在本质的穿越。她的第一本诗集《黄昏纪念册》聚焦于对日常性的描写,却也流露出诗人对内部世界的观察。诗集中的《祈祷》一诗被称为茨维塔耶娃的第一篇文学宣言。[4](15)小米袋整首诗洋溢着青春的激情,激情之下隐藏的是诗人对生命、对创作之另一面的向往,比童话更美妙,/不如再给我一个死①(①本文所引茨维塔耶娃的诗句均由汪剑钊所译,限于篇幅,下文所引不一一注出,详见《茨维塔耶娃诗集》,2011 年。),死亡在诗人的生命中获得了肯定,死亡是照亮生命的奇迹,茨维塔耶娃渴望在生与死的两个领域中不断滋养自己从而达到生命的完满和充盈。茨维塔耶娃研究专家萨基扬茨指出,《祈祷》——仿佛是伸展羽翼,隐含着对生活与创作的志向,[4](14)不断的向上飞翔的感觉是茨维塔耶娃诗歌中标志性的姿态,也是诗人自身渴望飞向高空所代表的永恒存在的象征。如果说茨维塔耶娃的诗是日常生活与存在矛盾驱动下的自然表达,是诗人现实生活与存在本质的天平两端博弈相长的产物,那么《祈祷》一诗的写作则是在诗人现实生活和诗歌世界的天平尚保持充满张力的平衡时进行的,全诗充满了生活的热情、浪漫的想象和对理想的向往,带着与生俱来的叛逆和自嘲,彰显了诗人对生命、死亡、上帝、艺术、自然的态度,预示出诗人的未来:我觊觎一切:我会唱歌儿我爱十字架,爱绸缎,也爱头盔……/不如再给我一个死……
诗人在《黄昏纪念册》中的最后一首诗《再次祈祷》预见了她未来创作中呈现的矛盾与冲突。诗人被这些漫长的日子折磨得痛苦不堪,她虔诚地朝向自己心中的拯救者——基督上帝跪拜,祈求上帝将她的灵魂安置在安谧的王国中与理想的爱情做伴。诗人习惯于以倔傲的姿态凌驾于尘世的一切之上,诗中写道:不需要以亵渎神灵作为代价的微笑不需要以受辱为代价的幸福,诗人是用这样傲慢的姿态来抗拒现实的庸俗,是用这种退让式的拒绝拉开自己与尘世的距离,从而获得灵魂与理想世界在意识中的进一步接近。没有悲哀,又何来幸福?/没有死者,又怎会有朋友?痛苦与幸福、死者与生者的二元对立自此开始贯穿了茨维塔耶娃一生的创作,在诗人那里,痛苦和死去成为能生成和赋予更高意义的幸福和生命的精神存在。在最初的幸福的写作中,她的整个、整个欣喜的灵魂开放如鲜花,诗歌创作对于茨维塔耶娃而言是从现实的尘世生活中上升到灵魂的、精神的启示与满足的过程,是从沉重的现实世界过渡到灵性的诗歌世界的契机。诗歌的写作本身也是一种语言的积极抵抗和对心中希望的肯定。正如诗人所说:诗人就是那种超越(本应当超越)生命的人。[1](102)小米袋
爱情是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然而,在她的笔下,相爱的人总是天各一方,无法走到一起。俄国著名学者洛特曼指出,浪漫主义的思想源于人类关系中的单一性、孤独性和分裂性,在俄国浪漫主义传统中,从莱蒙托夫到茨维塔耶娃,爱情总是决裂,是分离。[5](168)小米袋茨维塔耶娃对尘世爱情的拒绝和对诗意而崇高的灵魂之爱的向往,构成了茨维塔耶娃诗歌中尘世之爱与精神之爱的矛盾冲突。《平和的游荡生活》《八月——菊花开放》《两棵树》《爱情!爱情!……》等早期诗作抒发了生活与爱情带来的短暂的欢乐;《脉管里注满阳光》《我走在平台上》《我在岩石的板壁上写》《普绪赫》等诗作开始呈现诗人对灵魂之爱、天空之爱的无限向往;《我想和你一起生活》《你的灵魂与我的灵魂是那样亲近》是诗人对于她和爱人无比亲近甚至融为一体的美好爱情的幻想,然而两人之间始终横亘着一条精神上的鸿沟(一个是尘世的,一个是精神的);《没有人能拿走任何东西》《致勃洛克(组诗)》等诗展现了诗人对于相爱的人始终是各处一方、无法汇合的悲剧爱情观。她不接受尘世间的爱情,如她所言:残酷的尘世生活/人间爱情!她渴望在词语中相触、在精神中相遇的灵魂之爱,爱情活在语言里……,因而她在诗歌的语言中表达着自己理想的爱情。长诗《山之诗》和《终结之诗》是诗人描写爱情的巅峰之作,女主人公所追寻的纯粹的精神之爱超越了生活与世俗,虽与恋人的尘世之爱有过瞬间的交集,却因无法调和的矛盾而最终分离。
诗中对死亡的不断追寻是茨维塔耶娃对尘世生活进行抵抗的最高形式。同时,死亡也是一种求生的方式,诗人渴望穿越死亡到达彼岸的诗歌世界——诗人的天堂。死亡即意味着永生,死亡成为脱离尘世生活走向更高生命意义的过程。《祈祷》一诗中诗人对死亡充满向往,如今我会渴盼奇迹,死亡之于她是一种奇迹,是比童话更美妙的另一种新生;在《一次又一次——您》中,哑巴——在和人交谈……/正午——我蒙受灿烂的星光……/死人从骨灰里站起……,物品的反叛预示着诗人内心对世间规律的颠覆,而诗人自己也向往由生到死的蜕变:天使长把我带到断头台。《莫斯科组诗》中诗人的诗意遭遇到世俗的羁绊:我如同飘曳火苗一般闪动的眼睛——已经被一些陌生的铜板所冷却,诗人渴望重生:今天是我神圣的复活节(加注:基督徒认为,复活节象征着重生和希望,为纪念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之后第三天复活的日子。),新近逝世的贵妇人玛琳娜——从今往后什么都不需要。诗人已不需要尘世的一切,她的精神是富有的。在《在那些日子,你就如同我的母亲》中,诗人期盼着那一天的来临,——我将死去,——你也将死去,她认为,死不是灭亡,死是新生,它能把不可逆转的——时间还给了我们。《致勃洛克(组诗)》中出现诗人之死的主题:却把他推向死亡。/如今他死了。永远/——哭泣吧,为死去的天使!同样在《致阿赫马托娃(组诗)》中,作者幻想尚健在的诗人阿赫马托娃死亡,其实是作者在考虑诗人的命运(死亡)。《我知道,我将死在霞光中》多么希望,让生命的火炬可以熄灭两次!……/我知道,我将死在霞光中……/为着最后的问候奔向宽宏的天空……,作者幻想自己是天空的女儿,有着天鹅的灵魂,最终归宿是宽宏的天空,这是作者始终追寻的诗人的天空,是诗人灵魂栖息的场所。《西彼拉》中,在尘世被叫作/死亡的东西——是朝着苍穹的坠落……/在尘世间,合上眼帘——是朝着光明的坠落……/死亡不是沉睡,而是起来……,死亡在诗人笔下是朝向天空的出发,是朝向光明的前行。《瞬间》一诗中,作者欲以诗人的永恒来校正尘世中瞬间的错位,诗人是以死亡的永恒对抗尘世万物的喧嚣错乱。《我向俄罗斯的黑麦问好》一诗中,把手伸给我——到彼岸世界吧!/此岸——我的双手没有空暇,困顿于生活琐事的诗人更向往灵魂栖息的彼岸世界,彼岸在诗人心中日益明晰。小米袋
艺术即自然。[6](105)小米袋……除了自然(也就是灵魂)和灵魂(也就是自然),再也没有任何东西让我感动了。[6](107)茨维塔耶娃所说的自然是诗人本身,诗人是艺术(即诗歌)的化身。对于茨维塔耶娃而言,构成诗人生命的艺术是神圣的,她以艺术为生,艺术即是诗人的灵魂。[2](233)艺术亦是茨维塔耶娃诗歌创作中最关注的主题之一。在《野性的意志》一诗中,诗人脉管里澎湃的激情,与生活的风浪搏斗,充满斗志的诗人赢得了世界。在《致阿霞》一诗中滚开,谷包和面粉袋/我们是射向天空的箭矢,诗人明确表示厌弃日常生活中的事物,渴望离开地面向天空的方向出发,在诗人那里,天空是与大地相对立的更高的世界,是诗人灵魂的居所,我们是——出自威廉·莎士比亚的两行诗歌,诗人是诗歌的化身,承载了诗歌所有的美。在《致拜伦》一诗中诗人借对英国伟大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怀念来表达自己对伟大诗人的崇敬和对诗歌的热爱,诗人完全沉浸在诗的世界里。《在漆黑的天空中,——画着一些词句》的标题已彰显出诗人在现实生活和自己崇高使命之间抉择的结果,诗歌的灵感——轻轻袭来,尘世的一切慢慢隐退至后,生存意识(存在,即诗歌精神)再次取得胜利。《把别人不需要的,——都给我》诠释了诗人对诗歌、对艺术炽烈的爱与激情,诗人的生命由于爱而变成熊熊烈火,烈火燃尽黑夜的一切,带来了充满光明的世界,这正是诗人要坚守的诗歌世界。在《上帝》一诗中诗人的上帝与诗人融为一体,诗人的上帝披着浪漫主义的斗篷,[7](227)不断运动正在离开我们,飞向永恒——诗人的高空。《诗人们》是茨维塔耶娃对诗人存在本质属性的解剖,茨维塔耶娃笔下的诗人从远处引导着话语,被话语远远地引导着,诗人以诗的方式把他的体验形诸语言,让语言说出自己,诗人灵魂的世界借由语言打开它辽远的地平线,诗人的最终归属也是语言,因为诗歌从广义上来说即是语言。他甚至是自钟楼而腾起的人……彗星的道路——就是诗人的道路……,诗人在语言之间、自身的灵魂之间找到了力量生发的裂口,向高空腾起、向无限奔跑:是一辆大家永远赶不上的火车……。《生活》是茨维塔耶娃对现实生活的公然宣战。残酷的尘世生活如镣铐般禁锢着诗人的生命和灵魂,而他不可能让生活夺走我活的灵魂,诗人是刀尖上的舞者,在巨大的痛苦中展示着自己的诗歌技艺。诗人等待刀尖已经太久,他随时迎接着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试与生活诀别。在《切开脉管:生命止不住地》一诗中,诗歌的血液在脉管中流淌,艺术已是生命的一部分,不可割舍。
✦小米袋✦
二、小米袋
语言形式层面的统一:意义与声音的小米袋
相似联想小米袋
俄国著名文艺理论家加斯帕罗夫指出,茨维塔耶娃的诗歌是按相似度串起的联想,她成熟期的诗歌仿佛就是那种诗歌思维的浓缩物,是隐喻的链条,相似性联想的链条,再无其他。[2](138)诗歌是以隐喻为基础的。隐喻的基础是:人与自然的基本相似性,或人与大地的视同对等。[8](5)茨维塔耶娃诗中隐喻通过相似性的力量创造出无尽的变化和变形,诗人在万物之间,和人与万物的无限相似性与同一性中穿越世界,在一件事物中去寻找另一事物、另一个自我;在生命中寻找高于生命的东西,在死亡中寻找高于死亡的东西,从而建构起置身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意义上的链条。具体到诗歌中,从每一首诗当中,到每一首个体的诗之间,再到这些诗与茨维塔耶娃整个诗歌创作历史之间,都存在着一条由词语、形象、声音、副歌、韵律形式等勾连起来的形式链条,以最具象的方式呈现了主题上的统一。
评论家常提及茨维塔耶娃在诗歌技艺上的不断创新和尝试。回顾茨维塔耶娃的整个创作生涯,从《黄昏纪念册》(1910年)稚嫩的日记体抒情诗行到《里程碑》中对谚语、绕口令、四句头等丰富韵律形式的使用,再到20世纪20年代诗人钟情于突然爆发或突然中断的韵律,诗歌修辞特点急剧转变,以至于对组诗、长诗体裁的征用等,都体现了茨维塔耶娃不断试图用新的形式来呈现新的主题,以表达自己的内心感受。正如茨维塔耶娃在诗中所言,我知道,维纳斯是双手的事业,/我是手艺人,——我懂得手艺,诗人在诗歌形式上的选择远远不只是形式上的考虑,形式是诗人内心感受表达的外在载体,内在于诗的表达之中。小米袋
从茨维塔耶娃成熟时期的诗歌中,我们常看到相似性联想的链条:诗的标题给出核心形象,然后是一连串的联想形象摸索着层层递进,使核心形象逐渐明确。例如在诗人写给库兹明的诗《两道霞光》中,起初诗人将炯炯有神的眼睛②小米袋(②茨维塔耶娃1921年写给库兹明的信中谈到两人初次见面的情景,其中茨维塔耶娃着重描述了库兹明如两颗黑太阳般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隔着一百俄里也看得见。)之光喻作两道霞光,然后是两面镜子、两个焦糊的黑圈、两个极圈、两个黑乎乎的坑、两个太阳、两个深孔、两个金刚钻,最后是——镜子一般的地下深渊:两只致命的眼睛。诗人通过相似度串起的联想逐渐明晰了眼睛的形象,这些相似的联想形象是诗人对眼睛的意义诠释,眼睛是光与暗、火与冰、太阳与深渊、现实与记忆的矛盾集合体,它超乎自身的物质性,成为心灵、精神的象征,是现实世界通往理想世界的窗口,它介于人间世界与超人间世界、短暂与永恒之间。[7](261)《少年》组诗中的诗句少年的眼睛迷茫!失落/在蓝天!乌黑——蔚蓝!和《不再独断专行》中的诗句星星一般的眼睛,明眸——两座空灵的湖,/上帝的双重启迪,诗人不断在探索眼睛的象征意义,从普通的比喻联想升华到对大自然、上帝的想象,关注的焦点从之前的现实世界逐渐转移到超乎日常的精神世界。诗人从远方引领着话语。诗人——被话语引向远方,茨维塔耶娃如是写道。茨维塔耶娃善于用词语检验主题,用系列相似性的联想形象明确核心形象,而这些相似性联想形象的象征意义已远远超出核心形象本身的意义,它们是诗人对人生的思索在诗歌中的具象呈现。诸多类似的相似性联想如同隐形的形式链条穿插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与主题链条相呼应,并验证着诗的主题。
在茨维塔耶娃的诗歌中,我们常看到相同的词语或者意象贯穿在前前后后的诗中,形成了诗歌语言形式上的反复效果。例如组诗《莫斯科》中的钟声一词遍布在从第一首直到最后一首的每一首诗中。在第一首诗中,我也将得到自由的梦,叮当的钟声,/万冈可夫墓地的早霞,钟声在这里是自由与信仰的象征,诗人渴望灵魂的自由,心中满怀对上帝的信仰。在第二、三、四首诗中,钟声预示着爱情的到来。第五首诗中,钟声象征着信仰的力量,诗人预借震响的钟声表达对腐朽制度的不满。第六首诗中,钟声是诗人朝圣者走在卡鲁加路上的伴奏。第七、八、九首诗中钟声伴随着新生与死亡的主题交替,钟声是能洗除痛苦的魔音。悠扬的钟声回响在城市的上空,同时飘散在诗歌的每一个角落,钟声象征着诗人心灵的放空、对高空的渴望、对自由的向往。钟声的飘荡看似离散不可及,感官上的离散却被意义上的聚合所平衡。组诗中的钟声源自莫斯科红场入口处的伊维尔斯克钟楼,它是诗人内心对上帝信仰的回声,洒落在诗人对爱情、对死亡、对人生、对自由的书写中,把崇高的精神从高高的神圣世界传送到尘世(钟声从高往下传)[9](82)小米袋。钟声一词构成了强大的联系,以至于虽然每首诗主题不同,每首诗中的钟声却透露出诗人坚定的内心信仰和对自由的向往。不同主题的书写都是诗人内心感受的外在表达,诗人的内心始终充满着她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厌倦了你们,敌人,厌倦了你们,朋友,她怀揣着对上帝的信仰:不停地划着十字,踟蹰在一条歌曲的、美丽的卡鲁加道路上,去寻找诗人心中的上帝。茨维塔耶娃一生钟爱的意象比如霞光、火焰、天空、山峰、十字架等都在创作中反复呈现,诗人赋予这些事物形象以某种主观上的象征意义,这些意象成为诗人表达哲理观念的载体。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词语反复其实是她内心感受通过诗歌语言多次的外在表达,语言形式的反复加强了诗歌语意表达的力度,同时串联起诗人创作中的多重主题。
茨维塔耶娃在《良心光照下的艺术》一文中写道:诗歌应反映民族的和自然的声音,并沿着声音的轨迹前行。[10](90)小米袋茨维塔耶娃在创作初期已开始运用词语的谐音,她晚期创作的诗歌更加注重声音和词语词法成分方面的深化,诗人试图在这些方面捕捉到最终让她说出无法表达的东西的深意。例如在《磨面与磨难》一诗中,诗的标题磨面与磨难(Мукаимука)彰显出词语的谐音,两个俄文单词字母完全相同,重音不同,重音在后意为面粉,重音在前意为痛苦。面粉是日常生活中的物质,痛苦是精神上的折磨疼痛,茨维塔耶娃通过词语的谐音戏剧性地表达出诗人在日常生活中所经受的精神之痛。在给帕斯捷尔纳克的献诗《距离:俄里,海里……》中,诗的主人公已经不是词语,不是词根,而是前缀、词尾。一组通过前缀、词尾聚集起来的词语通过声音相谐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诗歌宽广的意义场。前缀рас-有分开、分散之意,它聚集的声音相谐词语语音上的一致性突出了横亘在诗人与帕斯捷尔纳克之间遥远的距离,同时,这些词语声音相谐的发音特征极大地增强了诗歌的韵律感和震撼力。长诗《山之诗》的献词中出现了谐音一致的两个词语——山峰(гора)和痛苦(горе)。在茨维塔耶娃笔下,山峰是心灵的居所,是真正爱情的象征。[11](272)痛苦(горе)一词在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经常出现,是日常生活与生存意识的矛盾带给诗人的内心体验在诗歌中的语言呈现。如诗人所言,她在自己的山峰上,把自己的痛苦歌唱。城市(город)和山峰(гора)在语音上的谐音一致与意义上的相互对立形成鲜明对比:城市在长诗中象征平庸的尘世生活,而山峰象征高空的心灵世界,二者格格不入。这样的例子在茨维塔耶娃的诗集中俯拾皆是,尤其是中晚期的诗歌中,诗人善于循着声音展开词语的逻辑,经常使用按照声音来选择词语的辅音重复法,以及词语、诗行的重复,都加深了形式上的一致感。
同时,茨维塔耶娃的诗集中不乏对修辞手法、语义结构、韵律等形式特征的关注。列夫金娜指出,茨维塔耶娃的个性化诗歌语言越来越向纵深发展,直奔语言形式和意义的本质,揭示出语法中不曾写过的,但却又是语言中固有的,并成为诗歌表现力的东西。[12](59)小米袋奥尔洛夫在对茨维塔耶娃诗歌的解读中提到韵律是茨维塔耶娃诗歌的本质与灵魂,他认为韵律服务于诗歌的内在形式,创造诗行的律动,使其焕然一新。[2](326)什列莫娃曾经探讨过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对立和悖论的精确性,她认为,对立是茨维塔耶娃诗歌意象的基础,揭示事物隐秘本质的对立,就像对界线的超越,使不能共存的东西彼此相遇,通过新奇的视角接近潜在的实质。[2](287)天与地、精神与物质、新生与死亡、灵魂与肉体等对立结构在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大量使用渲染出诗人对人生的感悟——厌弃了尘世的日常生活,渴望纯粹的精神世界,在死亡与生命、永恒与尘世、彼岸与此岸之间决绝的态度。对立结构在诗歌中从始至终反复出现,勾连起了茨维塔耶娃一生的创作,也构成了茨维塔耶娃诗歌语言形式存在链条上的重要一环。
✦小米袋✦
三、小米袋
个人创作与文学传统的统一:
现实与记忆、个人与历史的关联
茨维塔耶娃诗歌中更广义的意义传承在于她的个人创作和她所浸淫的文学文化传统之间的紧密关联。尽管茨维塔耶娃认为:我从未受任何人影响。[13](157)小米袋诗人的这一表述彰显的是她诗歌创作中自成一体不拘一格的个性,然而,时代思潮、文学文化传统必定对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如科尔金娜所言:茨维塔耶娃的创作是源于她个人的生活经验和她从阅读中汲取的他人心灵经验的印象。[18](155)茨维塔耶娃自幼在家庭浓郁的艺术氛围中成长,饱读俄国诗人的作品,接触德国浪漫主义的经典,深爱古希腊神话,在灵魂深处了滋生了终生不衰的浪漫主义精神。因而她的诗歌既带着深深的民族文化烙印,也浸染着德国和希腊的文学文化传统;她的诗歌既不自觉地受到她所接触的文学文化传统的向心影响,又在创作中寻求个人声音的自由和个性。
纵观茨维塔耶娃的作品,她的创作本身就充满着对个人和民族传统的自觉。普希金是我的理想,我创作的支柱。[14](73)小米袋普希金死亡事件以及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致大海》等作品极大地影响了茨维塔耶娃对诗人、对爱情、对艺术、对人生的理解和认知。茨维塔耶娃在组诗《致勃洛克》中提出了诗人之死:人们想——他是个人才!/人们却逼迫着他去死。在诗中茨维塔耶娃挚爱的诗人勃洛克是温柔的幻影,无可挑剔的骑士,却难以被人们理解,被生活逼迫得无路可走。关于诗人之死应追溯到茨维塔耶娃在幼年时看到的图画上的普希金之死,普希金之死犹如不可磨灭的烙印自幼便深深地刻在茨维塔耶娃的脑海中:普希金是我知道的第一个诗人,我的第一个诗人被杀害了,这为后来茨维塔耶娃在创作中诗人之死主题的提出埋下了伏笔。茨维塔耶娃称普希金与丹特士的决斗是诗人与俗子(普希金抒情诗中的永恒的人物与日常生活中的世人)的决斗,自此之后她将世界划分为诗人和众人两个对立的部分。[14](75)诗人与生活的对立在茨维塔耶娃不同时期的诗作中反复出现,多年以后茨维塔耶娃哪一个诗人不是被杀害?质问的提出再次印证了由普希金之死引发的诗人之死主题贯穿了她创作的始终。爱情是茨维塔耶娃创作中的另一个核心主题。六岁时的茨维塔耶娃爱上了普希金笔下奥涅金与塔吉娅娜分离的爱情,如她所言:我观看的第一场爱情的戏事先注定了我未来的一切,注定了我心中的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14](94)在茨维塔耶娃的意识里,只要相爱,就一定会有离别。两者不可分,只有分别时才能懂得爱。[15](121)相爱与分离的爱情悖论自此开始,繁衍出枝蔓,延展到茨维塔耶娃毕生的创作中。《叶甫盖尼·奥涅金》对茨维塔耶娃而言是一个启示性和基础性的文本,分离的悲剧几乎成了茨维塔耶娃爱情诗创作的背景和注脚。长诗《山之诗》所描述的渴望精神之爱的女主人公与只有尘世之爱的男主人公之间不可调和的爱情悲剧,似乎有着《叶甫盖尼·奥涅金》中奥涅金与塔吉雅娜之间爱情悲剧的印记,都曾有过瞬间的爱情交集,都因心灵的无法交融而最终分离。在《终结之诗》中,男女主人公有了最后一次短暂的约会,又与普希金笔下奥涅金与塔吉雅娜相见的场景如出一辙,相见并不意味着结合,相见是分离前深情的告别,分离是必然的结局。茨维塔耶娃深谙普希金的诗,她写道,每一个涂改处/都像出自我的手,茨维塔耶娃将普希金的手艺融入到自己创作的手艺中,以至于她诗中的意象、场景、观点、技艺等与普希金的诗遥相呼应。大海是茨维塔耶娃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是她童年时常抄写诵读的普希金《致大海》中的核心意象。茨维塔耶娃对大海意象的钟情源于她对普希金和对他的诗的热爱:当年我‘走向大海’其实是走向普希金的胸怀……走进普希金的心灵。[14](123)茨维塔耶娃认为,《致大海》是象征诗的自由的自然力[14](124)的诗人写给象征自由的自然力的大海的作品,她认为诗人或许还暗示了另一种自然力:抒情的自然力,正是普希金这首诗中的诗与自由成为了茨维塔耶娃毕生的追寻。后来茨维塔耶娃创作的世上的自由只有三种:歌曲—粮食—和大海大海的理想,大海的理想!大海是我们的洗礼池等诸多关于大海的诗句中,大海亦是自由和生命力的象征。茨维塔耶娃创作意识里的大海是普希金的自由的自然力的大海。茨维塔耶娃认为普希金在诗中对大海的爱是因诀别才产生爱,她自己与大海因未见却向往因相见而不爱,[14](125)诗人将自己充满预见性的悖论分离与相爱同样用来阐释自己和普希金,试图将自己与伟大的诗人相关联,她在诗中说:我是曾祖的同事/我们在同一作坊做事!
生活在俄国浓厚的宗教氛围中,受到作为东正教徒的父亲的影响,吸收了浪漫主义文学中的多神精神,茨维塔耶娃在潜移默化中拥有了宗教意识。传统基督教教义中的死亡、天堂、彼岸、永生与茨维塔耶娃在诗歌中所追寻的精神信仰有某种程度上的契合,尽管她称自己不是宗教教徒,她仍无法摆脱宗教对她的影响,她将宗教传统为我所用,为构建自己的信仰空间提供支撑。纵观茨维塔耶娃的全部作品,上帝、十字架、天堂、祈祷等宗教词汇以及圣经中的人物和故事以各种形式反复出现并贯穿于她一生的创作中,形成了茨维塔耶娃创作中的信仰之链条,成为诗人笔下诸多主题表述的精神旨归。茨维塔耶娃一方面继承了基督教传统,她相信上帝、基督和天堂的存在,从《圣经》中汲取人物形象、主题、故事以及语言;另一方面她带着传统的恩泽却又背弃传统,试图寻找诗人自己的上帝,构建与加尔文宗上帝的天堂对等的诗人的信仰圣殿。她提出:最好是我们的基督上帝加入他的(诗人的)诸神行列中。[16](363)小米袋茨维塔耶娃早期诗歌流露出的大多是对上帝的尊崇,对上帝赞美诗式的吟诵:十字架闪烁灿烂的金光……阳光下,基督的面庞多么温柔我开始梦见上帝报喜节的那一天,我的节日!,但也有对天堂和上帝的质疑:——天堂也没有幸福?十字架被扔弃!/在新的梦呓中我去寻找/新的深渊和星星,还有对基督上帝提出的悖逆的祈求:基督和上帝!……啊,请让我去死。③(③在传统的基督教义中神爱人,不愿让人去死。)茨维塔耶娃逐渐开始改写基督教信仰的标志性词汇,赋予它们新的意义,以此来表达她自身的信仰:大地的女人,在我呀——是天堂的十字架!/每晚,我只向你一人膜拜。十字架是基督教神圣不可侵犯的标志,代表着上帝对人的爱与救赎,而茨维塔耶娃将她喜爱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喻为十字架,是对传统宗教信仰的反叛,她试图在传统信仰的模式中寻求自己的精神皈依。后来里尔克成为茨维塔耶娃心中的上帝:你是父亲的宠儿……你是圣父的约翰,她再一次以宗教字眼为依托树立了自己的诗人的上帝。但是基督上帝并没有从茨维塔耶娃的意识中消失,基督上帝和她的诗人的上帝又是同时存在的:上帝与构思同在!上帝与虚构同在!,有时她又渴望基督上帝来保佑诗人的创作:上帝保佑!上帝永在!诗人命该如此。在茨维塔耶娃生命的最后,她写道:是时候了——是时候了——该把票还给上帝了,在她意识的根基里,基督上帝的天堂是生命最终的皈依,而诗歌,具有与上帝同样的神圣性,是诗人追寻的信仰圣殿。宗教意识伴随了茨维塔耶娃的一生,是她强有力的精神支撑,渗透在她的诗歌创作中,成为贯穿于诗作中的稳固的信仰链条。
茨维塔耶娃的文学修养较多来自古希腊神话传统和德国浪漫主义文学传统。诗集中对希腊神话人物和诸神的多次描写(例如代表心灵的普叙赫、天与地、黑暗与光明等)都例证了希腊神话传统对茨维塔耶娃的影响。希腊神话中的悲剧色彩和酒神精神也深深地感染和影响了茨维塔耶娃的创作。她的创作中日常生活与存在不可调和的悲剧性矛盾,对尘世现象的否定、对人向世界本质回归的终极探寻,以及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无意识创作,都与希腊神话中的悲剧与酒神精神相契合。尼采在阐释关于希腊酒神精神的著作《悲剧的诞生》一书中写道:悲剧把个体的毁灭表演给我们看,以此引导我们离开现象而回归世界本质,获得一种与世界意志合为一体的神秘陶醉。[17](10)小米袋不难看出,希腊神话以及尼采哲学对茨维塔耶娃的影响。如她所言:尼采就是(这种现象)。而且我们同宗荣洁在其专著《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研究》中用大量诗歌文本分析例证了茨维塔耶娃对尼采思想的吸取。茨维塔耶娃的诗歌创作也浸染着德国浪漫主义的色彩,比如对内在的心灵世界的抒写,写内心的追求和理想,善于用基督教思想统一人的意识,追求彼岸、来世、无限、永恒等,这些源于茨维塔耶娃自幼年起便受到德国文学的熏陶,浪漫主义思想在她一生的创作中如影随形伴随始终。
1941年8月茨维塔耶娃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生命。忍辱负重的生活压折了诗人高贵的翅膀,为诗歌而生活的信念把她推上了十字架:她等待刀尖已经太久!人称她的自杀是一场悲剧,而她在诗中说:在尘世被叫做死亡的东西——那是朝着苍穹的坠落,或许诗人是借助死亡来寻求生活之外的真理。茨维塔耶娃的一生不卑不亢,不落窠臼,永远守着自己心中的精神家园,她倾其一生的诗歌追寻,都是日常生活与存在矛盾斗争的结果与表达,是她诗歌信仰追求之路的呈现。诚如叶·科尔金娜所言: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的诗学个性是多种面貌的,她的世界观是矛盾的,她的命运是极具悲剧性的,然而她的诗学世界却是完整统一的。[19](155)小米袋
参考文献小米袋
原文刊载于《俄罗斯文艺》2018年第3期
图片来源于网络
排版 | 王紫晴
校对 | 谭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