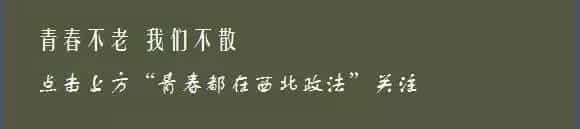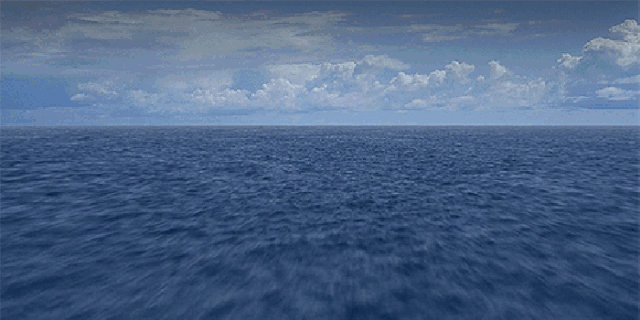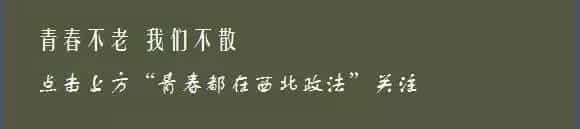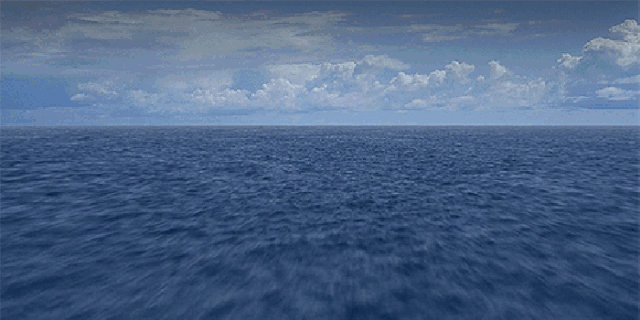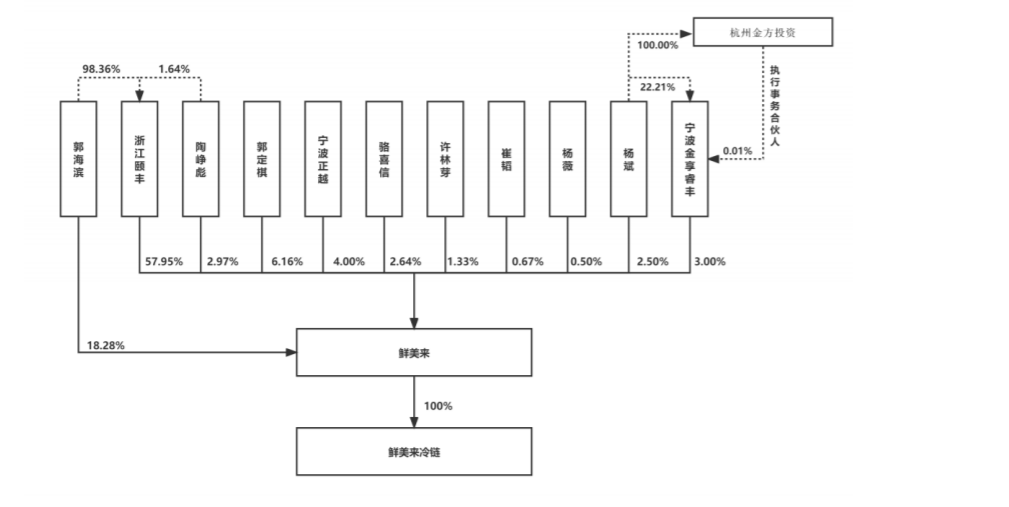奶奶的粉条渣
admin4724年前0条评论
她不是去扫大街,扫大街的话这笤帚太短,扫大街也用不着带帆布袋子。她是去附近的国营菜场捡菜去了,带把笤帚是为了扫掉落在地上的粉条渣。我奶奶捡菜不是因为家境困难,她和我爷爷都算革命干部,都有退休金的,我爷爷的退休金还不低。我奶奶是个过惯苦日子的细发人,我们这里的细发就是指在生活上很节俭,很精打细算的意思。她一张口就是民国十八年“遭年馑”( 关中话“遭年馑”就是闹灾荒的意思)时怎么怎么恐怖,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时怎么怎么难熬。讲一个我记忆深刻的吧:民国十八年遭年馑,穷苦人家都缺吃的,有位母亲还把为数不多的树皮无纺布面粉袋生产厂家电话/微信:15838231350草根麸皮之类的食物让给她的一对儿女吃,她饿了就喝水嚼树叶。结果她被活活饿死了。她的一对儿女趴在母亲身上痛哭,父亲也很悲痛,但他不让娃娃们哭。他说要是邻居们听到了,会吃了母亲的。他们家买不起棺材,于是就用烂席子一裹,趁着夜色把母亲的尸身埋在了自家屋后。第二天早上,他们发现这位母亲的尸体还是被人刨出来,干瘪的身上为数不多的肉几乎都被割光了……这种饥荒年代熬过来的受苦人,细发是正常的,不细发才是不正常的。当时买菜只能去国营菜场,菜场周围又有好多的家属区,需求量还是蛮大的。菜场送菜的卡车每天上午过来,车厢里总有两三捆红苕粉条的。两尺来长的大捆红苕粉条,没有袋子或箱子,就是用塑料绳在中间随意一扎。那时的红苕粉条都很干脆,所以每次粉条卸货时,多多少少都会掉一些粉条渣在地上,多则四五两,少则一二两。断裂掉落的粉条渣细碎分散,没办法一根根捡拾,我奶奶带着小笤帚就是来扫拢这些掉在地上的粉条渣的。她把粉条渣合着地上的尘土、瓜果壳、甚至烟头等,用笤帚扫拢成一堆儿,然后再用帆布袋子装起来带回家。到家后,她先把这些混杂着异物的粉条渣里大点儿的垃圾挑出来;接着再把还有灰尘及细小的垃圾的粉条渣用清水冲洗干净;然后放到大竹筛子里晾晒到干透;最后入袋时再戴上老花镜细细地挑选两遍。我现在还记得她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拨拉着粉条渣挑东西的样子。这些粉条渣就收拢在大的蛇皮袋子里,堆放在阳台的角落里。我奶奶在次卧门后放了一杆木秤,她时不时会把那些粉条渣过下秤,有时会叫我搭手抬袋子或看秤。她秤粉条时虽然不说话,但脸上满满的全是满足的样子。我们那里包包子、做菜盒都喜欢放粉条。当时肉少,半斤肉做个菜也就一盘子底儿,不够吃,也不过瘾。但把肥肉为主的半斤肉切成小丁,豆腐切丁,粉条渣泡软,再放上木耳、虾米,剁些葱姜末,调好半盆馅儿,配上酵头老碱做的发面,蒸成肉包子,可以有二三十个呢。蒸好的肉包子,皮都泛着当时罕见的油光,咬一口,肉丁已经将肉香传递给了同一个面皮被子里打过滚儿的豆腐丁、粉条渣、木耳丁等难兄难弟,大家都有了“高贵的”肉味儿。顽固一些的虾米、葱姜末,也是半为肉味半为己,残余的本味用来衬托肉香和味道的层次是再好不过的了。在当时的北方,包包子没有粉条,就像炸酱面没有炸酱,番茄炒蛋没有蛋一样。要调和各种馅料之间的味道,让它们达成天地之间的大和谐,非身材修长、品性温婉、谦和包容的馅料君子粉条不能胜任。再者,其它的馅料都是蒸了后要出水的,而包容兼并、求水若渴的粉条是吸水的。这样蒸出来的包子才不会一咬飚出一股不是那么鲜美的汁水,烫伤心急的吃包子的人。扯了半天,其实我觉得它易膨胀才是当时流行拿粉条做馅料的主要原因。蒸包子最坍台最丢人的就是瘪瘪的、馅料不足,一股子小家子气。有了便宜易膨胀的粉条,家家都能蒸出体型饱满呼之欲出的包子了,皆大欢喜。我是从乡下来城里借读的,本来就内向羞怯敏感,我奶奶在菜场捡菜扫粉条,常常让我觉得颜面扫地。我平常上学放学,都会绕着菜场走的,生怕碰到在捡菜扫粉条的我奶奶。有时我奶奶捡得菜多了,拿不动了,她就会把菜放到路边某个角落里,让我去拿。我都会觉得很尴尬,甚至觉得屈辱。快到过年时,我奶奶会把这些粉条渣分装成四个小袋子,有的多一些,有的少一些。每年过年,我爷爷奶奶都请我爷爷的单位派辆小汽车,送我们回约四五十公里外的乡下老家过年。我爷爷奶奶住在西安,我也在这里借读;我爸爸身为建筑工人,跟着工地项目到处走;我妈妈我哥哥我妹妹在乡下老家。我二姑家离大马路还有两百米,有条狭窄泥泞的乡间土路从大马路通往她家门口。车到了大马路和乡间土路的路口时,我奶奶让司机停车,指着后备箱一袋粉条渣和捆在一起的其他年货,让我爸扛着去送给我二姑。我很怀念去年这时候路过我二姑家,她给大家做的水煮荷包蛋,我觉得挺好吃的。我想问车不开到我二姑家去吗?但我又不敢问。我爸沉着脸,嘟囔两句,扛着这些东西下了车,顺着有点泥泞的狭窄的乡间土路往我二姑家去了。司机说,陈师(师是师傅的简称,西安流行这样称呼人)好像不高兴啊。我奶奶脸上露出看破一切的笑容说,嫌给他妹子东西了,心疼。我爷爷戴着老式军帽和深色的石头镜,披着有毛领的大衣,坐在副驾驶位上,一言不发。不一会儿,我爸就回来了,我二姑跟在他后面,过来问候我爷爷奶奶。车子继续开,到了村东头我小姑家,我小姑和我小姑父闻声出来站在街边门口迎接我们。我奶奶又指着后备箱一袋粉条渣和捆在一起的其它年货让他们搬走。我奶奶会喜笑颜开地和小姑说一阵儿话,小姑是她最小的女儿。我记得我小时候看过我奶奶歪歪扭扭的日记(我奶奶没念过书,只上过扫盲班),很短很干巴巴:某年某月某日,今天广政来西安了,把翠引跑了,我很伤心。我爷爷戴着老式军帽和深色的石头镜,披着有毛领的大衣,坐在副驾驶位上,仍旧嗯两下就算回应我小姑了。回到西头我家了,照例会有一些乡里乡亲来探望我爷爷奶奶。碰到年纪大一些的、辈分高一些的,我爷爷也会和人寒暄、聊天,虽然并不热烈。蒸包子了,我奶奶地指着装着她捡来的粉条渣的袋子对我妈阔气地说,粉条多放一些,管够。到了灶火间,我妈会低声说,又不是肉管够,烂粉条渣渣,谁稀罕呀?我妈不稀罕,有人稀罕。在那个收入有限、物资匮乏的年代,还会有人来找我奶奶买粉条渣。别人买好后,我奶奶经常会再抓一小把添给人家,说我这可是西安的粉条,质量好得很,明年再来啊。附近新开了一家号称西北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我奶奶的捡菜事业越来越兴旺了。粉条渣她已经不扫了,看不上;蔬菜批发市场里的粉条流通量很大,短于十厘米的粉条,我奶奶都懒得捡了。我奶奶捡的菜越来越多,越来越重,随着她年纪越来越大,拿不动的时候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一年一年的长大,一天比一天更加敏感羞怯,一天比一天抗拒去帮我奶奶把捡来的菜和废品(是的,我奶奶后来除了捡菜还捡废品了)拿回家。虽然我抗拒这件事,但我还是做了。听话这两个字就是我的外壳和牢笼,我躲在里面心有不甘、日渐生茧。于是,我后来离开爷爷奶奶去别的地方复读初三,我仍旧没考上中专,但考上了老家县城里的省重点高中。我离开爷爷奶奶时,对于不用再帮奶奶把捡来的菜和废品拿回家这件事,有如释重负的感觉。我那时在山东胜利油田某采油厂,接到电话后我红着眼在路边拦车,无人理睬。还是一位巡逻的交警问明情形,用摩托车载着我,帮我拦了一辆去北京的大巴。我从北京辗转回老家,在县城回老家的中巴上,我碰见我二姑的大女儿,她问我怎么回来的。我虽然对于奶奶的去世仍旧伤心,但还是略微大声地说,我从“北京”回来的。我奶奶去世后,本来就不爱说话的我爷爷,就更加不爱说话了。他经常搬个小板凳,坐在阳台上原来奶奶捡粉条渣的地方,拿着把放大镜,看报看书。那些书都是讲红军、八路军、解放军打仗的书,那时他还是曾在延安为党中央站岗放哨的英姿飒爽的革命军人,后来他也曾南征北战,在山海关所在的军队整体转业了,有好多照片为证。那时的奶奶也还年轻,我大姑还是名小女孩,我爸爸和另外两个姑姑甚至还没有出生。八十年代有一阵儿,我奶奶每天早上七点钟掐着点儿出门,她夹着把一尺来长的自制小笤帚和一个帆布袋子,步履匆匆。

微信号:15838231350
添加微信好友, 获取更多信息
复制微信号
本文作者陈明,西北政法94级经贸系校友, 现在上海从事律师工作。
(本文首发于作者公号“明律如是说”,转载请联系该公号。)
本文链接:http://mianfendai.cn/post/983.html